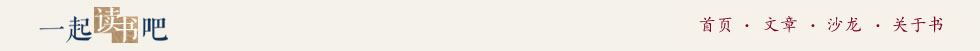一起读书吧468期,今天观点君跟你分享安妮弗朗索瓦的这本小书《读书年代》,它的副标题很文艺,叫“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
你旅行的时候会带一本什么书?
| 弗朗索瓦:卧病在床:姑婆、妈妈和我
我能读那么多书,首先要感谢生病。
起初是一个长年卧病在床的姑婆,自己琢磨出一套小学教师的育人理论,决定教我识字。她其实不是我的什么姑婆——每户人家都有那么几个牵扯不清的假亲戚。事实上,她是我祖母的德国侄女以前的英语老师(说得够清楚了吧)。除了我的玛德莱娜表姑,即她以前的学生之外,我想也只有我才能忍受富尔夫人,也就是被我们尊称为姑婆的夫人。
在我这个小孩的眼里,她老得至少有两百岁了。她订阅了所有的杂志,身边总是围着一堆书,坐在床上运筹帷幄,主导着“珍珠”(La Perle)的文化生活。皮埃尔叔叔有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赶去圣艾蒂安的书店取回她订购的书籍。每个沾亲带故的亲戚家的孩子,识字之后都要被召集到姑婆跟前结结巴巴背诵字母表。最大的孩子在床边给她念书,小一点儿的要接受知识测验,大人们也得依照指示温习哲学书籍。每年暑假,文学恐怖笼罩着位于上卢瓦尔省的圣西戈莱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竟然没有人背叛家族选择做文盲,真是奇迹!
四岁的我还不够格参与这些活动,便被派去给姑婆充当杂役,掸刷她床单上巨大的绣花,收拾书本,拍打枕头,帮她挪动台灯或者拉开窗帘。我喜欢这份差事:她不仅不抱怨我带去的果酱饼难吃,心情愉快的时候还讲故事给我听,而且不全是用来说教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她就按捺不住好为人师的冲动,发誓要在假期结束之前教会我识字。懵懵懂懂中,我给自己锻造了奴役的锁链。
有一段时间,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开始惧怕她的热情,幸好,我要提前回巴黎了。悲哀的是,妈妈见我学得如此投入和辛苦,决定亲自教我认字。后来人们惊愕地发现,在花样百出的教导之下,我竟然没有学会大声朗读,甚至偶尔还会口吃。
姑婆究竟是病了还是老了?我想可能是病了,因为若干年之后,有一次我告诉她我“生吞了几个鸡蛋”,她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那时,我已经到了读《呼啸山庄》的年纪,姑婆还活着。
在这两段插曲之间的几年,我自己也时常生病,这和读书不无关系。早上,只要体温降到39.2度,我就有权看画报,因为人们觉得读画报不累人。我总在怀念那些快乐的上午:我坐在乱糟糟的床上,妈妈戴上擦澡手套帮我洗漱,用古龙水抹遍我全身,帮我换上干净的睡衣,把我抱到躺椅上,给我盖上鸭绒被。然后,她打开窗户,开始整理床铺。干净的床单、鼓鼓的枕头、新鲜的空气,这一切令人愉快,尤其当我发现妈妈在拍打过的被子下面藏了两本《淘气鬼莉莉》和《米老鼠》,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因为我知道妈妈从骨子里讨厌“愚蠢的”儿童读物。
后来,妈妈染上肺结核住进了医院,而我被送去了寄宿学校。妈妈在医院里没完没了地注射对氨基水杨酸,也读完了欧仁•苏和蓬松•杜•泰拉伊的书。
《巴黎的秘密》让她格外开心(她实在不该!),以至于不得不改变要读的书目:她总是看得哈哈大笑,笑声引发了致命的咳嗽。医生暂时禁止妈妈读书,于是她决定把《茶花女》和《波西米亚人》改编成亚力山大体的四幕悲喜剧(妈妈的努力当然都以失败告终)。
一年以后,我们俩都回到了家,家里还多了个佣人昂里埃特,是个红头发的诺曼底女人。她的厨艺很好,可妈妈几乎不碰她做的菜。有时候,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妈妈突然觉得饿了,昂里埃特就趁机为她做蔬菜炒鸡蛋或者奶油小牛肉片。她渐渐发现妈妈这种突如其来的饥饿感是读侦探小说引起的,于是在买菜回来的路上,她就去书店翻翻黑色悬疑系列,只要书里能找到三明治、香肠和硬壳蛋这些词,她就买下来。运气好的时候,她能说动妈妈尝尝她拿手的兔里脊肉。她称呼妈妈为“夫人”,以第三人称和妈妈说话,对她尊崇得五体投地。只要暴风雨一来,她便躲到妈妈怀里,请求我们切断电源、放下百叶窗、关上窗户。这时,妈妈会为她端来一杯橙汁,还轻轻洒几滴在她的太阳穴上。
如果那个时候就有热爱美食的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侦探小说,妈妈也许还活着,而昂里埃特肯定已经成为兼营诺曼底和加泰罗尼亚美食的餐厅主厨了。
摘自《读书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