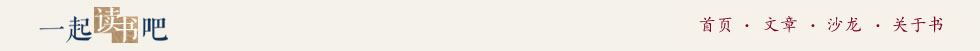9月6日下午6点16分,在北京爱琴海单向空间书店一个持续了八年的酒局“六根”六位作家的六本新书与读者见面,这也是单向街第760场单谈沙龙——《醉醒客》系列新书发布会。 《醉醒客》系列是六根酒局上,六位中年男人所著的六本书系列名称。分别是首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辉的《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诗人、学者,《凤凰周刊》主笔叶匡政的《可以论》;时评人、影评人韩浩月的《错认他乡》;人民网读书频道前主编,最热门的荐书人绿茶的《在书中小站片刻》;《南都周刊》主笔、《新京报》专栏作家潘采夫的《十字街骑士》;《文史参考》前执行主编、时光网副主编武云溥的《生如逆旅》。 分享会像他们以往的酒局一样备上了酒,分为三场。六根还请来了出版人杨葵、读库主编老六和话题系列主编杨早做嘉宾。 杨葵:慢慢描摹自己的故乡,它会给你很多 每次我开会都拿一本书,里面夹很多小纸条,被很多人讽刺,说假装看过全书,今天是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刚才在那儿紧急补了补两个人的序,好在他们两个人的文章我经常看到,跟潘采夫认识的时间久一些,看到的东西也多一些,跟韩浩月是头一次见,但是也算是神交已久。这个地方总共就这么大,也就这么几个人在写文章,所以我先做这个开场白,以你们两个人说的自己的故乡为主。你们都刚看到书,别人看到的更晚了。 这场派给我们的任务是讲故乡,但是特别惨的是我没有讲故乡的概念。曾经有一个同学在酒局上讽刺我,说我们都有故乡,你怀念故乡的时候怀念什么?我说我不是北京人,我生在江苏淮阴的地方,具体到涟水县,好像也有很多历史故事,但是我都不知道,像你们说的窦娥的故事等等,我是长大以后才知道一些关于涟水的历史。但是这些东西和我没有连接,跟故乡也连接不上,按说也在那儿生活了11年,我曾经住在涟水县城的五金公司的员工家属院里面。 我们院儿处在县城和乡村的交接地,是一个库区。里面有一半的地儿装满了五金公司的那些东西,主要是自行车,有当时最红火的,永久、凤凰、飞机自行车。所以我非常会装自行车,现在那种老牌自行车,两分钟我就拆光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曾做一个义务工作就是帮同学修理自行车。院里另外一半就是家属区,有几排平房。 说起来能讲的也有很多,以前我自己也写过一些关于江苏的事情,可是都不是故乡的概念,也不像一个故乡的概念。刚才说要聊故乡,我现想了想,讲这些可能不太得体。 故乡的意义更多的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境上的概念,对过去事件的浓缩。所以可能是过去的一种玩具,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至今在北京还生活着的人,他对一个儿时玩具的心态和心理,跟我们日常所说故乡的概念也很相近。 八十年代初,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句话耳熟能详,叫知识就是力量。但是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阅读思考越来越深入,我觉得这句话说反了。知识反而是越有就越觉得自己非常薄弱,非常无力。我记得有个哲学家说“知识就是腐败,知识容易带来腐败”,大概是这个意思。当你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容易特别拿这个当回事。 回过头来说故乡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和心理上的那个过去,或者我们叫故乡,反正就是那么个东西,当你跟他拉开一定距离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故乡更容易掌控?还是你发现它其实是更难掌控?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东西,曾经有过的一些心境,一些状态,那些状态带来的到底是手拿把攥的,十拿九稳的东西,还是更有敬畏心?随着你对故乡越来越了解,你对它是更热爱?更敬畏还是更什么? 所以我想说的是,故乡这件事既然是一个过去,还有一个距离上的东西,我们不妨把它放到更大的一个坐标系里面去考察。就是当你考虑到全球化的时候,你就觉得山东跟河南或北京之间就没什么差别了。当你放到整个太阳系里面的时候,这个点就彻底忽略不计了。 但是,做事情应该有一种我个人的倡导的“大处着眼,细微处着手”的方式。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可以往太阳系思考,但是我们着手的时候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划,像韩浩月和潘采夫一样,慢慢描摹自己的故乡,它会带给你很多收获。 韩浩月:如果我老了,不会回到老家 我的故乡是山东最南端一个叫郯城的地方,和江苏接壤,我要说我家乡的话,会有一部分像山东话,一部分像江苏话。 我们家乡政府部门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它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典故,郯城嘛,郯城有一个名人叫郯子。说他是孔子的一字之师,这个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们这个地方一直拿这个事大做宣传,我们自以为是孔子的老师的地方之一。 另外就是窦娥冤的原形发生在郯城县,我每一次回家经过窦娥的墓的时候,还会去独自站一会儿,一年可能有十来个人去看就不错了。曾经我们的政府觉得作为发生窦娥冤的地方不太光彩,所以很值得推广的事情却被大家淡忘了。 我这本书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写我在郯城生活的一段时间,其实我出生在农村,是一个乡村的青年,后来到了县城,从那之后到现在我都自称为小镇青年,小镇青年现在看起来还是要高一个档次的。写的就是我来到县城从上初一起的十年生活,这十年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写县城、写故乡写不出好东西,觉得已经写空了。40年之后,直到去年,突然觉得自己回过头来看写过的最满意的文章,最突出情感的文字,还是写10来岁那会儿的东西。还是那些一直我想遗忘却到现在也忘不了的东西,也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故乡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心,觉得从这么远的地方突然到了我以为我在中国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对它充满探索的心理,甚至有一次经过地下通道的时候都会觉得兴奋,都会觉得自己是在穿过一段历史。 在这儿生活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对我的吸引力已经远远不像我刚来的时候那么强,其实这种从心理层面来讲,就是寻找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在现实生活当中,曾经被我不喜欢,被我厌恶、讨厌的东西真的重新又出来,重新唤醒我的记忆,重新回到我的生活方式里面。 我想起我在现实当中,骑着自行车,在下过雨的路面上飞快的骑,骑得非常快,前面有一个石子,自行车轧上去了,结果我飞出去五六米,后来就趴在路面上。开始是起不来,后面是不想起来,下着大雨自己就趴在路面上是一件特别诗意的事。后来再去回想现实生活,确实是人为会给它加一些诗意的东西,包括后来给广播电台写散文稿等等,骑着自行车送到里面,电视台的台长我经常送稿子,所以成了特别好的酒友。我最幸福的一个事就是我在工厂休息的时候,听着县的电台播我的文章,经常是一个女播音员,声音特别好听。类似的事情有很多。 后来为什么不太喜欢回到故乡,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找到答案了,还是喜欢故乡的那个生活方式的,喜欢那里面熟悉的街道和场景的,但是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发现和故乡的人在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不再是我十多年前那个时候那帮老乡,包括我的亲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是我不太想承认的,但是确实在发生。如果我老了,我不会选择回到我的老家去生活,这是一个既矛盾又痛苦的事情。 潘采夫:他说,你们写了很多伪故乡 我实际上每年都会回去几次,回到老家村里面。但是我后来自己意识到,我写的这个故乡的东西跟我去到那个村子没什么关系。 我经常会对农民题材的写作批评,或者批判,超过很多旁观者,就是因为你实在是了解太多的东西。但是写到文章里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个字去写他们的这种大非,或者写他们坏话。 我们之前在南京做活动,一个大学生说,你们写了很多伪故乡,你们把你们想象的东西安插到这个书里面。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有时根本不忍心写,怕破坏你童年对乡村的想象。所以把它写得很宁静、很美好,就像沈从文当年写乡村的时候,如果是冷眼一点的旁观者,你会发现他写的东西本身也很残酷,但是他写的时候很温情。 有故乡的人、能回忆故乡的人,比没故乡的人要好一点或者多一点东西。我们是有很多回忆,这是相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的。像我女儿这样,她生在我们老家,很快回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有七八年,又去了国外,去国外几年又回北京待着,他们成了世界人。 我越来越多地碰到这样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具有世界人的特色。你问他什么是故乡,他完全不知道,而且他完全不在乎,他觉得你有故乡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种族优越感?我没有故乡的概念,这个词从我这儿消失掉了。我们书写它会觉得比较美好,有哀愁。但他可能没有故乡也没有什么缺憾,也许就是一个时代发展,这个词就掉了。 绿茶:进入阅读需要契机 六根酒局已经持续了八年,这八年来我们吃遍了北京东部大大小小的馆子,参与了我们六根酒局的朋友也至少有一两百,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封闭的酒局,我们每次会邀请我们的一些朋友来一起来参加。2014年的6月6号,我们就开通了六根这样一个公号,发着发着就被我现在的同事美女编辑杨爽看上了,就有了这样一套醉醒客丛书。 这本书里面主要还是一些关于我这些年和好书的相遇,还有和好书店的邂逅。这让我对阅读这个事情特别的上心,自己也享受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所以《在书中小站片刻》,实际上是对我自己这种状态的理解和表达。因为我觉得,人和书的相遇以及它能够变成你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剥不开的情绪。我和书就是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那种关系,作为一个书评的编辑,其实我和书反而没有很多藏书家或者爱书人那么深切的感情,因为我很多的书都不是我自己买的。 进入阅读是需要一些契机,或者是一些巧合的。我进入阅读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在一个书店做店员,那使我和书本之间产生了关系,并且影响到我后来每次选择的过程,这是一个机缘巧合。其实我们这代人缺乏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但是有很多阅读巧合能够让一些人真正进入阅读,比如我跟杨早做读书会,这是能够让人进入阅读的方式,让阅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契机。这个是阅读和人和人之间的巧合。 叶匡政:阅读意味着你在被入侵 我们准备买一本书跟我们到商店买件衣服和杯子不一样,买个杯子是使用,买衣服也是,其实我们到单向街准备买一本书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头脑可能会被别人的思想会入侵。 你只要在阅读,那就意味着你在被入侵。我们判断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往往是认为如果增进读者的智慧或者理性,我们通常会觉得这就是一种有价值的阅读。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一种是非常合理的阅读,不是理性的阅读。我们这个社会经常把“合理性”和“理性”是混淆的。这种阅读其实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合理性。那么理性的阅读,我个人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更应该提倡的,所谓理性的阅读,“理性”的关键在哪儿? 第一,理性可能会关注普世的价值,强调的是你关注理性的人类的普世价值为首要原则的。它会把这些普世价值,定义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但是合理就不是,合理往往强调的是一个集团或者一个个人在当下的特殊利益,比如我最近需要干什么了,我就读书。 第二,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强调自律阅读,而不是他律的阅读。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虽然书店里有大量的书,但是有默默的力量为我们挑选,他们决定我们能够读到什么,或者不能读什么。所以,重要的是读者要有判别的能力,把善和恶的知识区别开。一个时代,一个成熟的公民,或者一个成熟的公民的美德就是他能判断善恶知识,通过阅读使自己成长。 我1969年出生,生长在阅读的黄金年代。我们开始成长的时候是正好八十年代,那个时代一下的书全来了,我们通常把那些书放在一起,把《荷马史诗》、卡夫卡等等所有的作家都是混在一块儿看的。我们那个年代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书一下混进来看了。 而且那个时代相对来说基本只有阅读。那个年代所有的偶像都是作家、哲学家、诗人,不知道有什么歌星等等,我们那代人是静态的。阅读是单向的,写作是一个人在写,读书也是一个人读,同时是封闭的,必须是一个人沉浸在里面。 但是互联网不一样,微博、微信不一样,你写一个东西,很多人跟你在分享,你再回答,也能构成阅读。对于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年代成长的人来说,我们认为,人类世界所有的文明的经验或者社会上我们认为的理性智慧的成果都保存在书中,所有重要的经验都保存在这儿。 现在有了互联网,会把一些知识稀释,或者通过影像,通过各种方式稀释,也能进入阅读。但从大环境来讲,单向阅读或者封闭性的阅读,是不是能够传承? 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变化,一个是从纸的阅读变成电子阅读,另外就是文字变成图像。图像就是使所有年轻人回到一个跟原始人差不多的状态。原始人没有数字,像苏格拉底,像佛陀他们都是反对印象文字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文字,包括伯拉图、孔子也反对,他的论语是他的弟子记载的,他们认为文字只有讲出来才是可以交流的,他们认为可以交流的思想才是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因为印刷品的流行,这种观点就变化了。 印刷品时代认为,只有保存在纸上的才是真理。 杨早:阅读是反人性的 当阅读量足够大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有知识,一本新书进来不会那么陌生,很快会被归到一个位置上去,这个要说很清楚,这个可以增加我们阅读的数量。 我经常回答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一个问题,阅读广义的说你看公微号,或者看微博,或者看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叫阅读。但是真正构成阅读核心的东西,实际上是要参与思考的,思考和进步才叫阅读。 阅读这个事情,我经常说是反人性的。因为人性趋易避难,阅读很多书是需要挑战的。你可能不要在最熟悉、最舒服的环境里面,你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同的东西。走出去的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 阅读这个话题很大。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小孩很容易反驳你,说你们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只能读书。现在有那么多渠道,为什么我们要读纸书。关键不在于怎么读和读什么,而在于你能不能够一直保持一种思维和追索的习惯。 我记得2007年读书会的时候,邱小石说过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他们这些公司的人跟你们这些学者或者是文人也好的区别就在于你们可以三个小时谈一个话题,而我们三个小时已经谈了十个话题了。但是事实上后来通过阅读邻居的推广会发现,每个人都能够三个小时谈一个话题。因为阅读就是一种带动你的思考,让你不断去进入事物,而且了解周边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走一个电子游戏里被黑云覆盖地图一样,大家知道那种感觉,世界在你面前更加清晰。这个是我们阅读的一个想法和想象。 老六:我们怎么记录一个人物?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除了爱看书之外,还爱看电影,很多人家里收藏了很多影碟。史上第一禁片是哪部电影?在座的知道吗? 我记得当年我去卖盗版碟的商店里采货的时候,那个老板非常神秘的把这张碟给我了,这个没有封面,就是《意志的胜利》,这个被很多国家列为不能让年轻人看的一个电影。我最近看到一个话题就说,《意志的胜利》这个电影让年轻人看,会有30%的人会爱上法西斯,剩下那70%再看第二遍,大概一半多就全都投入到法西斯的怀抱了。我也看到过很多对希特勒的描述,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是一个公认的恶魔,但是他最成功、最闪光的年代,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是什么? 我看过有人说,为什么当年的德国人为什么要报票投给希特勒,一篇文章叫《为什么不把票投给希特勒》。当年希特勒在大选的得票率是90%多,人类历史上仅次于金正日他们。希特勒当年这么高的得票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媒体,我不知道德国有没有党媒,如果有的话,我们看他们的媒体对希特勒的描述,就像《意志的胜利》的胜利对希特勒的技术,可能所有人都会爱上希特勒。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和李辉老师和武云溥探讨的话题,就是人物,我们怎么来记录一个人物? 李辉:判断一个人物,理性非常重要 写人物是一个非常敏感、沉重的话题。 30年前,我当时年轻气盛,是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人,觉得我喜欢的人我就去采访,不喜欢就不采访。也就是说当时因为我对胡风比较熟悉,所以我对反对胡风的人,比如周扬等等这样一些人,我有机会采访,但不去采访。比如我因为采访沈从文,跟沈从文很熟,那么我就对骂沈从文的丁玲虽然有来往,但是没有去采访。 我那时候年轻,现在回想起来,是对从事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尤其我们作为记录人物的人、写人物的人,到了年过半百之后会慢慢发现,需要一个更宽容的心,或者更从容的心态了解你身边所有值得关注的人。后来已经来不及了,这些人都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观点,或者相反。但是对于还原历史、还原人物,是要方方面面都要尽量采访到,这才是立体的轴向。 所以刚才谈到希特勒也好,包括谈到文革时代的很多一些人也好,其实我们中国不仅仅是五六十年代以来,其实整个中国在五四前后,是缺少这种记录人物的传统的,虽然《史记》有、《汉书》有,但是总体是不发达的。五四以后胡适提倡写传记,所以那个时候有了郭沫若的自传,有了沈从文的自传,但是很多是文学性更多一些,缺少一种更严谨、客观、全面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代人很欠缺的功夫,这个功夫是要政治学、历史学基础的,包括采访技巧等等。 我们怎么真实记录一些历史,尤其判断一个人物,理性非常重要。在理性的同时,要有一种包容的东西,或宽容的东西,甚至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历史的架构,你才能对一个事情有一个提前的预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不知道的,不知道国家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你到这个年龄之后,可能有一些东西,现在觉得特别棒的事情,很可能五年十年前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武云溥:我喜欢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记录人物参照性不一样,其实挺难有对比性的。我们如何真实的还原一个人物的写作,一个办法是尽量多的找周边的人、在场的人。 我十年前开始当记者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两个问题很难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我真的很难去接触到特别大师的人物,因为那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可以称得上大师的人。另外是这些人讲的话,我没办法判别真伪。一个办法是我不去写大人物,我喜欢写的是大时代下面的小人物,什么叫小人物,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小人物,如果有大人物在,可能就要清场了。 老六:我们的记录能真实多少呢? 让我产生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见到过一对年轻人,他们做现在的口述实录。现在有很多人有钱之后想在给家里的老人祝寿的时候给老人整理一个传记,因为现在这种数码印刷已经有了,我就印三五十本,祝寿的时候分发给亲朋好友,但是这些人没有写作能力,或者没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就请这对年轻人写。 后来我问他们,他们真是全国各地到处跑,还有很多订单。我就问,你们对这些人的采访中有没有好玩儿的事?你可以想见,他们的采访往往都不好玩儿,因为子女是出钱的人,资方会要求这些人,我爸爸妈妈只能这么写,丑事不许提,坏事不许提。我开始很困惑,我说这兄弟俩干的这个事太痛苦了,太没有价值了。推而广之,我们每个人处在这个市场中都是要面临资方,面临管控方的要求,我们的记录能真实多少呢?你能回答我内心的困惑吗? 武云溥: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话是不可信的 我觉得这个看谈话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比如说像现在当着大庭广众说话这是一种方式,这种时候说的话基本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话是不可信的。 另外是密谈,私密地谈话。由于两个人身份、关系的亲密程度不同,他们讲的话的和谐程度,有的是要衡量的。像刚才你说的出钱,你给我爸写个传记等等,这个事是挺不好干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都喝多了,酒后吐真言,无话不谈。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过去的采访对象当中我是尽量跟他们私混,比如我在广州的黑人聚居区,三元里、小北那一带,有一段时间我奉命做一个选题,是广州黑人区的生活,我能跟黑人兄弟一起生活半个月,那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摄影/杨公振 编辑/杨公振、实习生范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