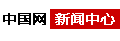李彦谈文学中的亲情困扰
李彦 (加拿大):亲情困扰可能疏解于笔端?
几年前,我应邀去多伦多,为一个读书会做讲演。那个读书会的成员,清一色都是白种人职业女性。她们对我的英文小说《雪百合》中的母亲这个人物形象,展开了意见相左的热烈讨论。
有的学者不解,为什么在我的几部中英文小说中,会反复出现围绕着母亲发生的故事。母爱是个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歌颂母爱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我读过的作品中,印象较深的,有高尔基的《母亲》,张洁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还有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在我成为母亲之前,我对母爱的理解是单纯的。在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对母爱的理解,却陷入了深深的惶惑。
长久以来,伴着岁月的流逝,我一直未能从对亲情的困扰中解脱。也许在潜意识里,正是这种惶惑,促使了我提笔创作。我抑制不住地试图通过笔尖,梳理出对亲情的反复思索,层层深化,以求彻悟。
我等待了十五年,才把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全部译写成中文版,呈现给祖国读者。尽管时光的沉淀,已使中文译本更趋成熟、客观,但仍然引起了母亲的愤懑。她扬言永远不能饶恕我。
我反复向母亲解释文学创作和回忆录之间的不同,她实在不应当对号入座。即便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亲人的一些伤心往事,我也希望她能有心胸,为记叙历史的真实而做出奉献与牺牲。
“妈妈,用不了多少年,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我对她说,“而历史应当存活在后辈人们的记忆中,才能使这个世界渐趋完美。”
母亲不能释怀,迫我反复向她检讨道歉。中国文化强调“为尊者讳”。父母面前,错的,永远是孩子,这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我虽在加拿大生活了27年,但我血管里流淌着的东西,至死无法摆脱。和母亲解释文艺规律,已无济于事,便只能无奈地任凭早该摈弃的文化糟粕一遍遍重复。
正如我在《雪百合》中所感叹的:真实,是十分丑恶的。
倘若我们如实地描写亲情,该有多么恐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曾写信给我,论及我的小说《雪百合》与李南央所著《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二者中存在的同样一种现象,纳罕是何种因素造就了这种特殊类型的女性。
这个问题很复杂,令我陷入了更多的思索。说真话很难。但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作者,应当坚持独立思考、客观地反映生活,而非趋炎附势、投机讨巧,随意歪曲或美化历史与人性。
不少人倾向于把一切不幸都简单地归咎于政治运动。然而,曹七巧的生活圈子里,政治运动是零。 即便是在政治运动繁花似锦的岁月里,众所周知,磨难与冲击也并未使所有的女性都丧失理性和母性,采用对敌斗争的手段来折磨自己的亲生骨肉。虎毒不食子。那是为人的底线。
不可否认,性格造成了命运。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一个又一个熟识女性的观察与分析,探索人性缺陷所引发的问题,由此造成了她们命运的坎坷。不回避这样的因素,我们才会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
刘再复老师在《红浮萍》的前言中曾有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分析:小说女主人公雯对于“父亲”(组织)的绝对的爱与忠诚,使她丧失了其他一切的爱,并经受了贯穿一生的身心折磨。
他的话,令我想起了多年前偶然读过的一篇英语论文,那是关于中世纪欧洲一个修道院里发生的故事。该文描述了曾经生活在修道院里的几名年轻的修女。她们都在暗地里把自己“嫁”给了耶稣·基督,通过对这位“恋人”的忠贞不渝,来维持信念,碧海青天夜夜心,渡过修道院里凄清孤寂的漫长岁月。也许,女性是依赖于“爱”与“被爱”来生存的。修女们为自己“爱”的本能找到了寄托之所,成功地实现了情感的转移。
爱,或者说亲情,是我的小说主人公对她母亲所寄予的悲悯情怀,同时也是小说中的母亲希冀获得组织认可时所孜孜追求的一种情感。
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家庭和亲情这些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在新的文化震荡之下被扭曲和破化。作为骤然投身于变革洪流中的知识女性,雯们无可避免地挣扎于新旧两种价值观中,一方面,她们渴望以独立自主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自立于世,一方面,她们在潜意识里却依旧摆脱不了女性在传统上对男性的心理依附。当这种依附无法通过美满幸福的婚姻得以完善时,雯们身不由己地将这种情感寄托到了男权的替代物—“组织”的身上。
这个强有力的男权替代物所倡导的斗争哲学,需要雯们在革命的蛹化过程中勇敢地割断一层层亲情的丝线,并使她们象在追求一个完美无缺、高不可攀的恋人一样,屡屡被拒之门外。她们的才华和努力都付诸东流,而从她们身边夺走这一切的,恰恰是她们最渴望拥抱的恋人。
造物主是仁慈的,乐于看顾不幸的人们。他早已为普天下的女性都准备了一剂医治心灵的良药。无论贵贱贫富,能够体验为人之母的过程,实乃人生之大幸。
可叹造物主的神情厚意,并非人人都能领悟。女性或者母性的情感无以寄托时,人性中恶的一面便会凸显。女性往往会逃避面对强势的男权,而选择相对软弱可欺的其他女性,作为报复的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此时也成为方便的工具,使得失意的女性能够名正言顺地把满腔怨愤都发泄到女儿的身上。当她们把女儿,而非儿子,看作一切不幸的根源之时,恰恰证明了她们远未摆脱开传统文化的桎梏,成为拥有独立自主平等观念的新女性。
雯们不懂得,博爱,才是治疗一切疾病的良药。悲悯和宽容,不掺杂任何目的的纯粹的爱,才是真正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们只能接受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时代和他人,从不反省自身的缺陷。
时代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僵化的口号消失了,代之以物质的诱惑。今天的人们,陷入了另一种困境。除了钱,已经贫穷得一无所有。面临着新的潮流,雯们的失落,使得她们的人生悖论愈加明显。可悲的是,这代人已入耄耋之年,大多衍化成性格古怪的偏执老者,已无能力站在时代的背景下,冷静地审视自己人生的得失,寻找到心灵的宁静。
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京,探望年迈的母亲。一个落日将归的傍晚,她突然悠悠地问我,“基督教如今在中国很盛行。据说,大多数中国人是为了祈祷钱财而信教的。焉知基督教的精髓,却是教导人们学会忏悔的。是吗?”
从母亲已经昏花的眸子里,我捕捉到一线微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