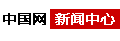陈瑞琳谈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历史挑战
陈瑞琳(美国):今日长缨在手----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历史挑战
在当今的世界华文文坛,一个非常独特又醒目的现象就是海外女作家所掀起的创作热潮,大有一马当先、不让须眉之势。
纵观世界文坛的发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学引领风潮,如英雄主义及自然主义,以及他们所塑造出慓悍、顽强、帶有不屈精神和奋斗内质的硬汉形象。
近一百年来,女性作家的创作才开始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从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曾有十二位女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还不算《简爱》的作者夏绿蒂,《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莉,《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远航》的作者维琪妮亚•吴尔芙,《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契尔等等。但尽管如此,在整体的世界大文坛上,女性作家的创作还是属于支流的力量。但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世界的华文文坛,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成为主力军!无论是亚洲地区还是北美洲及欧洲,华文文坛都呈现出一幅“山花烂漫”的女性风采,甚至是一马当先地冲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地前沿。正可谓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海外的“文学女人”应运而生。
解析当今海外文坛的“红楼”现象,一来女人与文学有着天生的血脉关系,生性中敏感多情,又渴望倾诉;二来海外的女人在生计的压迫上相对比男人少,因而更有精力投身创作。三来移民的生涯充满动荡变换,更加上当代的华文文坛风起云涌、内外交流,遂形成更丰富的文学土壤和环境,于是,被激励的女性文学即成为一脉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纵观海外女作家的创作,其主要的精神气质及情感表达,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在她们的笔下,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人”的冲突与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学千姿百态又自成方圆的风景。

近年来海外女作家创作的一个新特点,是开始走向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方向,她们能够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巧妙地切换,无论是历史的回首还是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不仅表现出“跨性别”的崭新视野,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当然,在海外女性作家高涨的创作热情面前,一个严峻的历史挑战也摆在面前,那就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将如何肩负起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坛的大使命?如何进入到更深重的人类命运的关怀,如何展现出“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显然是当代海外女作家所要面临的大跳跃。在观照海外女作家的地域性特征时,我们发现:东南亚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令人可敬,主要是表现在她们所拥有的自身造血功能和努力在近亲中吸取写作营养的品质。但由于她们缺少母语国的生活经验,对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又比较陌生,创作的土壤多局限在自己生长的原乡,急需要在题材上及表现手法上寻求突破。北美的华文女作家,目前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她们多属第一代移民,学养背景比较深厚,有深入血脉的母国记忆,也有面对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们的创作中,一个宝贵的特点是有意识地保持了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与“本土文化”及“主流中心”的心理距离,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写作空间。在大陆学者的最新研究中,跨文化的边缘体验为海外女作家所带来的不仅是敢于直面异域文化的勇气,同时也带来对母体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张翎的《余震》,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袁劲梅的《罗坎村》,王瑞芸的《姑父》等,都是与国内作家迥然有别的有关“中国故事”的书写。但是,在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中,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生命价值的探讨,她们同时也需要为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寻找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再看欧洲的华文女作家,已从上世纪的“散兵游勇”进入到“骑兵纵队”的方阵。生活在人类文明的源头,欧华女作家特别善于用他们的灵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达世界。但是,有关欧华女作家的研究却一直是相当的薄弱。比如:被誉为半部欧洲华文文学史的赵淑侠,其创作的拓荒意义并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更有她近年来创作的历史人物小说,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价值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本质也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阐释;英国作家虹影,其作品内在的女性主义力量也远远被忽视。当代法国小说家赵宝娟的创作,其勾人心魄的绝品小说,几乎无人问津。有关荷兰小说家林湄的作品,其中所张扬的宗教精神在学术界也是忌讳莫深。此外,近年来在法国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山飒,这位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孩所创作的小说《围棋少女》,在法国已经销售了12万册,并被译为英、德、韩、日等17种语言出版,作品先后获得法兰西学院奖、龚古尔处女作奖和新年奖、卡兹奖等,中文版的《围棋少女》也已在中国出版发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冷战结束后,统一后的德国逐渐取代了英、法,而成为欧洲文学的心脏,德华文学也随之兴盛起来,其中以女作家的贡献尤其显著。如麥勝梅女士笔下的德国風景,复旦才女穆紫荆的创作,新移民作家刘瑛的小说等,都有其特别的意义。除此而外,在欧洲的华文坛上,比利时作家郭凤西笔下的欧洲风情,西班牙作家張琴的文學空間,法国学者作家杨翠屏的创作,也都非常值得研究。由此可见,歐洲的女性文学创作正在踏入一個开花结果的成熟階段,她们的努力需要得到掌声。关于澳华女作家的整体评价,近年来虽然也是“众生喧哗”,但是很多作家都成为“昙花一现”。冷静剖析她们的作品,大多创作还属于个人的移民故事,张扬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学”中早期的猎奇题材和传记色彩,例如麦琪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有浓郁的个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则缺少大情怀和大关怀。因此,澳华文学需要在整合后再出发,在坚持中提高与升华。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坛,同时也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文坛,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与交流的一个桥梁。今天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已经摆脱了那种“无根”感觉,也逐渐摆脱了游子思乡、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巢臼,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与人类关怀。真正是在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更令人可喜的是,“海外文学”与“海内文学”也开始呈现出“融合”为一盘棋的趋势。比如目前居住在欧美的新移民女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所写的文字,和国内的作家已经非常相似。再比如大陆背景的作家与台港背景的作家也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当然,这“合”中有异,异中又会有同,可谓双向刺激,双向互补,而这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一文中这样指出:“以华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盪等現象來看,華文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質量最大最可觀的文壇。” 为此我们相信,本世纪伟大的华文作品,可以在中国出现,也可以在海外出现。